戴逸老师走了。1月24日一早,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刘仲华刚到单位,就从在中国人民大学做老师的昔日同窗那里听说了消息。和戴逸亲近的学生们有心理准备,他们知道老师从去年开始就住院了,一个月前已经无法进食,在ICU也待了一段时间,可是,他以前也进过ICU,但挺过来了,又转回普通病房,他还惦念着未竟的事业。
去年住院期间,在清史编纂委员会通纪组工作的刘仲华还给戴逸打过电话,汇报通纪稿件的修改进展。他躺在病床上也惦记着《清史》,因为他等纂修《清史》,用了半生时间,能够再次主编《清史》,他说过,这是“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戴逸的耳朵在多年前听力就不太好,需要助听器,这两年,即使戴了助听器听力也不大好使,身边的子女便成了接听电话的助手。电话里学生说一句,女儿便大声在病床上的他耳边重复一句。他得知道,稿子怎么样了。“本来想着,等老师身体好一点了,就把上次他说过修改意见的改稿情况跟他汇报。”刘仲华对《中国新闻周刊》黯然地说,“老师没等到我去汇报工作就走了,虽然有心理准备,可还是觉得,太突然了。”
2002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历史学家戴逸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时,已经75岁,他给很多人讲过他心里常想起的一个传说故事——干将、莫邪夫妇俩想炼一对锋利的宝剑,但总炼不好,最终,夫妇俩跳进火炉,以身铸成宝剑。

2017年9月,戴逸于张自忠路3号留影。图/IC
爱吃雪糕的老头
每次走进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段祺瑞执政府旧址旁边的小平房大门,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王琬莹看到的几乎都是同一幅画面,眉毛、头发已全白的戴逸伏案在书桌前,手边的稿件摞起来一尺多高,书房里到处是书,书架上,地上,桌上……“书虽然多,但收拾得很整齐,归类也清晰,可见老先生对自己的书,既爱惜,又熟悉。”王琬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二十来年,戴逸几乎都是这样过的,看稿,改稿,一直到住院前。“疫情没发生时,他还常到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办公室去,或者是参与编纂的学者到他家来。”刘仲华记得,通纪的稿子每完成一部分,他就要第一时间看,从初稿开始,每一页都贴着五颜六色的纸条,纸条上密密匝匝地写着修改意见,从观点到论据到引证再到表述,修改最多的时候有3万多字,全部是手写。
几年前,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美国清史专家欧立德拜访戴逸时闲谈,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戴逸笑笑说:“现在只看稿子了。”自从受命领头编纂《清史》,他就放下了自己一切学术上的事,把全部精力集中于修史。
刘仲华1998年考上人大清史研究所博士时,师从戴逸培养的中国第一位历史学女博士黄爱平,因为经常跑腿给戴逸送信,得以常常出入他家。在他的记忆里,戴逸老师也总是伏案在书桌前,只是那时候,他的头发还没有这样白,每年还都要写十多篇学术论文。作为新中国清史学科的奠基人,撰文、教学、会议、讲座……需要他做的事太多,他常常担心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担心“暮年多见世上客,未识真容已白头”,他几乎把能属于自己的时间,全部铺在书桌前,可这不意味着他没有“温度”。

2005年6月17日,戴逸(右二)工作照。图/IC
读书时,刘仲华担心自己学问浅薄,不敢和戴逸探讨学术,戴逸就开开心心和他眼里的“孩子”唠家常,他知道刘仲华的家远在新疆,每次送信的时间只要距离饭点不远,他一定把人留下来:“仲华啊,你就留这,一块吃饭。”赶上夏天,他多半要去冰箱里摸出两个雪糕,刘仲华一支,他自己吃一支。老家在江苏常熟,戴逸喜欢甜食,但他也不挑剔,每次出去参加会议,赶上什么吃什么,辣的也行。刘仲华感慨:“戴老师吃东西从来不挑剔,其实在任何方面他都是这样,待人宽厚和善,极好相处。”
无论他的学生,还是学生的学生,都不怕和他有争议。好几次,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一起开会,戴逸提出一个想法,副主任们统统反对。在委员会担任副主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马大正回忆,戴老师说,怎么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但他也不生气,坚持学术民主,所以大家都有什么说什么。有时候说了,他当时不接受,但是过了一两天,他会说“你们这个主意还是比我好”。戴逸喜欢下围棋,他有一句口头禅,“是不是我又下了臭棋了?”
2018年,人民大学出版社想为戴逸出一套《戴逸文集》,最开始他没同意。每次有人用“清史泰斗”称呼他,他总摆手:“不敢当不敢当,我只是个修史的。”不想出文集也是类似的想法,他总觉得,“不必吧”,“还不用着急出”。于是出版社就择机再找他商量,文集的策划编辑王琬莹回忆:“我们提请求,提了好几次,戴老师后来同意,感觉他有一部分考虑是愿意支持我们的想法。”
戴逸习惯照顾别人的感受,学生时代王琬莹在人民大学读书,去听过戴逸的讲座,老人有浓重的苏南口音,所以有意放慢语速,就怕学生们听不懂他的普通话。有一次戴逸出国参会,刘仲华帮他去银行换点外汇,老人过意不去,叮嘱刘仲华打车去,把打车的路费单独包好一并交给他。学术会议上,他也很少当面驳斥别人,“每次戴老师不再继续说了,我们就知道,嗯,他又保留意见了”。刘仲华说。
后来出版文集,刘仲华帮忙整理戴逸的文章,俩人有分歧,戴逸希望以时间顺序整理文章,刘仲华按照当今读者的阅读习惯,计划按文章的类型整理:“文史随感”、“书评书序”、“清史编务”……有些文章,鉴于体例,刘仲华觉得可以暂不列入。如今回想起来,刘仲华感慨:“他对别人的建议都认真考虑,不因为自己是长辈就固执己见。”他现在还记得,自己把道理详细解释之后,老师想了想说:“仲华啊,你说得对。”
戴逸的弟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在文章里写过,老师不遗余力地提携晚辈后学,胸怀宽广,兼容多样意见,“即使弟子的观点与自己的主张出现分歧,仍予最大限度的包容接纳。与先生受教论学,如书院中师生之间坐而论道,切磋辩难,洵洵有古风焉”。
小人书里启蒙历史
“戴逸退学了!”“戴逸考上北大了!”1946年夏天,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里一则爆炸性消息被传开了,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上海交大是名牌大学,铁路管理是热门专业,在那个重理轻文的年代,学铁路管理意味着金饭碗,学历史几乎毕业就失业。戴逸说,是童年时代的兴趣和爱好,让他走上了历史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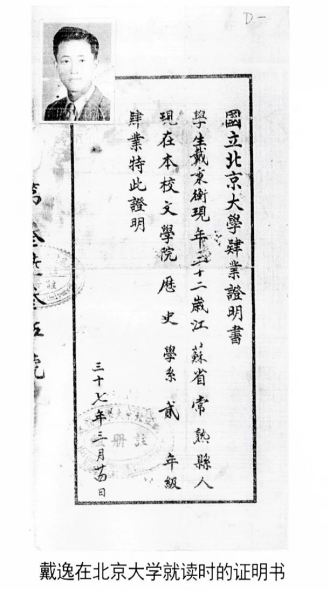
戴逸在北京大学就读时的证明书。图/中华文史网
江苏常熟,荣木楼,历史上是明末清初东南文宗钱谦益的旧宅,清朝大学士蒋廷锡的府邸就在边上,这是戴逸儿时的居所。那时,常熟城里有许多以出租连环画谋生的人,他们挑着担子,背着藤篮,走街串巷,一个铜板就可以租几本书——戴逸把家里给的零花钱全都用在了租连环画上。《三国演义》《水浒传》……看了又看,爱不释手。戴逸特别喜欢其中一位会“说书”的租书人,能把历史故事说得头头是道,人物栩栩如生,听得年幼的戴逸如痴如醉。有一次听得出了神,晚饭没有回家吃,急得家里人到处找他。
明清以来,常熟遍布藏书楼,虽经战火摧颓败落,街市上仍残存着数家古籍书店,店中陈满了各种线装古书,读者可随手翻阅品读,无异于一座座小型图书馆。年纪渐长后,戴逸经常流连徘徊其中,零用钱又一点点积攒,用来买书。日积月累,戴逸到高中时居然也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小藏书室。他在一篇自述中写过:“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独处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彤管,朱蓝粲然。”在戴逸的弟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看来,老师“治学文字中时现悠然古风,大致可溯源于此”。
1944年高中毕业后,完全从现实考量,本一心向慕文史的戴逸进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不过一年,抗战胜利,北京大学准备从昆明迁回北京,1946年暑假恰巧在上海交通大学招生,更凑巧的是,考试地点就在戴逸宿舍楼下。强烈的冲动促使他去试一试,结果被录取了,人生戏剧般地发生变化。
之后的几年,戴逸在北大听过胡适、郑天挺、沈从文、朱光潜等人讲课,又因为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辗转去了华北大学。戴逸就是那时候取的化名,他的原名为戴秉衡。
1949年后,华北大学迁往北京,改名中国人民大学,戴逸留校成为党史专家胡华的助手,从党史开始,走上了历史学道路。他的第一本著作名为《中国抗战演义》,书用章回体,他后来回忆,可能与少时读很多演义类书籍的影响有关,写这部20万字的书时,他只有25岁,虽显幼稚,却是他学术道路上的起跑点。
戴逸的治学,几乎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由近而远,先研究党史和革命史,稍后研究中国近代史,最后研究清史,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这是那一代学者身处的特殊时代所造成。
那时中国的史学界重视古代史,专家名流群集于上古先秦史。秦汉以后的历史,研究者已少。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研究者更少,几乎不被承认是一门学问。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一分为二,原有历史组单独成立中国历史教研室,由于缺少中国近代史教师,戴逸被调到中国近代史组,填补缺额。
考虑到国内没有一本完整的、适合高校授课的近代史讲义,戴逸决定撰写《中国近代史稿》。1958年,四十余万字的第一卷即告完成,此时他才32岁,这成为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
戴逸与清史结缘在1973年以后。那时,他从江西省余江县“五七”干校返京,和几个同事一起被分到北师大,在北师大内建了一个清史研究小组。那个时代,要求历史学界开展边界问题的研究,戴逸选择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一课题,用了四年,对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情况、条约文本和争议问题作了详细的研究,还从故宫查到满文中有关尼布楚谈判的奏折,写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这是他的第二部代表作,也开创了清朝边疆史研究的先河。
自此,他开始了后半生对于清前期和中期的研究,他前半生研究的中国近代史,包含晚清时期。北京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刘仲华感慨,戴逸是中国当代少有的贯通清代前后期历史的清史研究大家,“他不像现在的很多学者,如果研究政治史,就只关注这一领域,而且还分段,分古代史或近代史。戴老师的研究不光在时间上贯通,各个领域也都信手拈来。同时,他善于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讨论,他有世界的眼光”。
刘仲华至今清晰记得做博士论文《清代诸子学研究》时,戴逸给的点拨:做清代子学研究,不能只盯着子学,要把经史子集在清代的整个学术发展脉络搞清楚,而且不光要了解清人怎么探讨先秦诸子学,还得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子学的发展状况以及诸子百家的学问到底是什么,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视野之开阔影响了刘仲华后来的整个学术思想,融会贯通——这是他从戴逸的学术衣钵里感受最深的四个字:“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只关注自己的研究领域,要站在更高处,看见学术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这种时代背景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历史发展背景,还有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这样才能看清自己,理解世界。”
等待半生修清史
戴逸与纂修《清史》的缘分最初源于历史学家、北京市前副市长吴晗,他与吴晗的相识颇具戏剧性。1947年夏秋之交,戴逸是北大学生进步组织“孑民图书馆”的总干事,四处搜集进步书籍。有一次,他听说历史学家吴晗那里有一批从解放区带来的图书和文件,就直接去清华大学面见吴晗。那时,他刚刚读完吴晗的《朱元璋传》,自然抓住机会当面探讨,吴晗听了他的一番宏论,便记住了这个年轻人。
两人再见面已是10年后。1958年,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中国近代史稿》厘清了中国近代史的整体逻辑,作为学术新秀,被吴晗吸纳进“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同年,董必武提出编纂两套历史书的设想,一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二是清史。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周恩来总理专门找吴晗谈过清史编纂事宜。吴晗特意征询了戴逸的意见,两人一起畅谈了许多清史研究的想法。只是,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使得清史纂修工作搁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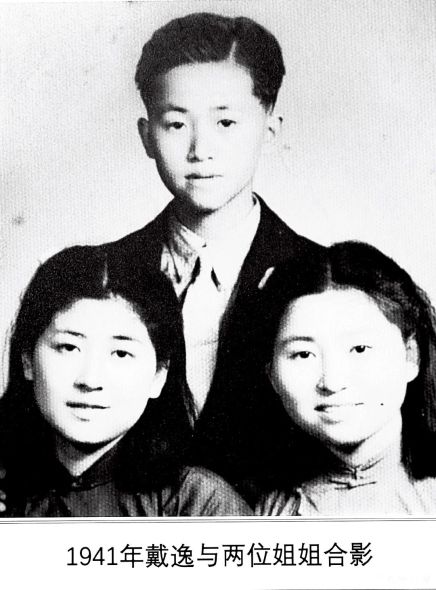
1941年戴逸与两位姐姐合影。图/中华文史网
1965年,筹划清史的编纂工作再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宣部召开部长会议决定成立由郭影秋、尹达、关山复、刘大年、佟冬、刘导生、戴逸七人组成的清史编纂委员会,并筹备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39岁的戴逸是最年轻的委员。不过,修纂工作很快又被搁置。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停办数年后复校,为编纂清史积蓄力量,戴逸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担任所长。他意识到当时社会上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清史著作,漫漫史卷,两百多年光阴,直接着手纂修大型清史未免陷入没有抓手的困境。于是,戴逸向时任副校长郭影秋提议先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清史著作,以梳理清代历史的主要脉络和线索,就这样开始了长达7年的《简明清史》写作。这是1949年后,第一部系统完整论述清朝历史的专著。
人和时代总是有密切的关系,时代创造人物,给人提供活动的舞台,而人的思想却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在时代的氛围中成长,反映时代的特色,执行时代的要求,解决时代所赋予的使命。戴逸觉得,乾隆就是这样的人物。60岁以后,他开始对清史里的人物产生兴趣,他选择了乾隆。乾隆档案有40函,还有4万多首诗,戴逸花两年多时间全部看完。在《乾隆帝及其时代》里,戴逸摆脱之前以论带史的传统,让人们第一次不用脸谱化的方式看待清代帝王。
钻研半生,华发满头,当年最年轻的清史编纂委员已经步入古稀,他一直没忘记这件事。时针走进21世纪,戴逸觉得时机已经成熟,2000年他在接受《瞭望》杂志采访时呼吁:“编纂《清史》,此其时也!”他的倡议迅速得到学界的热烈反应。2002年,清史纂修方案获得国家批准,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
近50年过去了,最早修史动议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多已谢世,戴逸是为数不多的健在者之一。等待半生,75岁的戴逸披挂上阵,出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他说:“我怎能不喜出望外呢?原来以为我有生之年赶不上了。”
编纂清史是一项浩瀚的文化工程,涵盖清代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卷帙浩繁,除了3500多万字的主体工程,还包括三类基础工程:国内档案整理、国内文献整理、国外档案文献整理,涉及国内国际学者近两千人。
此后戴逸几乎每天都前往委员会办公楼坐班、召集会议,既要把握总体,又要组织协调各个环节,他感觉自己肩负着几代史学家的托付。直到90几岁,才开始居家处理工作,但只要身体状态允许,他还要坐着轮椅、拄着拐杖到办公室去。20年来,他在和时间赛跑。
今日是昨日的延伸,真正的历史学家必然有一份现世情怀。戴逸常常感慨,清代是距离今天的我们最近的历史,这上下近三百年,包含着多少人物和史事,兴衰轮替,悲欢离合,胜败斗争,升沉起伏。有众多经验教训可供汲取,有无穷的哲理遐想可以反思。
他成天和这段历史打交道,有时感到,和这段历史如此贴近,我们今天的社会问题,大千世界中林林总总的复杂情态,追根溯源,几乎都可以在清史中看到它的根苗。要了解今天的中国,认识国情,清史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知识。有时,他又感到和这段历史相距如此遥远,它纷纭复杂、深奥多变,使人难以揣摩,留下了太多疑团。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近代何以落在西方国家后面?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何以如此坎坷曲折?中国在这几个世纪内达到了怎样的历史伟绩,又丧失了哪些历史机遇?这些恒久的追问,在他看来像斯芬克司之谜,历史学家寻遍资料,搜索枯肠,尚没有得出一致、令人满意的结论。
历史学家所做的无非三件事,叙述历史,考证历史,解释历史。而最终,是要解释历史——说明事情如何发生,因何发生,探究历史的因果,揭示历史的规律。戴逸觉得,自己一直整理和叙述历史,在解释历史上,只是有些尝试,三者结合是他渴望而未曾达到的理想境界。他曾多次和后学晚辈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做不到了,你们还年轻,一定要努力去做啊!”他在“历史编纂”上投入的全部热情、精力和自己毕生的学术积累,也许正是其学术理想的另一种寄托。
戴逸说过很多次,“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清史纂修的完成”,他觉得成稿可名“第一稿”,大家看了,发现优点和缺点,就打磨修改,再版,渐成佳作。他并没有想给历史什么定论,并不奢望清史纂修能够一揽子解决清史研究中的诸多疑问和争议,他只是想为后人留下这一代人对那段艰难曲折历史的思考,自己未能解答的斯芬克司之谜,也许后人可以。
他曾经数次感慨于历史学家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和历史内容客观性所构成的矛盾,“个体生命的不在场对漫长历史、遥远未来的视程有限”。
2024年1月24日8时12分,他终于得以超越了一切矛盾和局限,这个一生修史的98岁老人,不再修史,他融入了历史。
发于2024.2.5总第112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戴逸:一生修史
记者:李静
编辑:杨时旸